人间滋味
2024-04-07 18:59:57
短篇文学
15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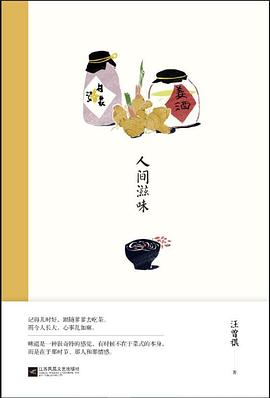 PDF
PDF
作者简介:
汪曾祺:
1920~1997。
他在短篇小说和散文创作上颇有成就。散文集《蒲桥集》《人间草木》等。
写字、画画、做饭,明明是最平常普通的日常,他却深得其中的乐趣。
不管在什么环境下,永远不消沉沮丧,无机心,少俗虑。这就是汪曾祺。
内容简介:
味道是一种很奇特的感觉,有时候不在于菜式的本身,而是在于那时节、那人和那情感。
活着真好啊!像汪先生那样去感受生活的乐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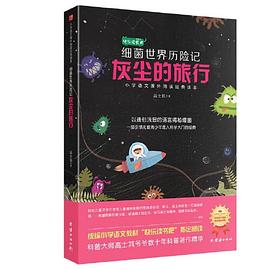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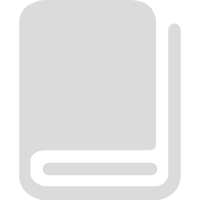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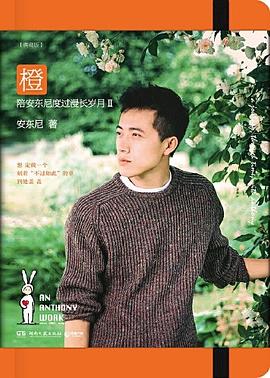
所有评论